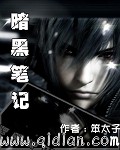���бʼ� by ��������-��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Ҳ���Ӵ����������Է����IJ����ɻ���ľ�����Ǹ����ϵ�ĸ�������һ������
�����Ҳ�Ը������ֻ࣬�����ι¶�������Լ�����������Ķ�����Ӧ�ڱ�Ѱ�ң�������ǿ�������������ӵ�еĶ�����Ȼ���ڣ�ʱ�̲�ȥ����˵������ı�����Ŀ�����Ĺ�����������ֿ��ܣ������Ŀ��������������ź���������ˣ�Ϯ��ÿһ����ǰ����
�����ⷬ�����ڻ�ɬ��ֻ�м����������˽����������������ҵĶ�ʮ���꣬���糨��������������ɫ�࣬��ѧ�ű�������������ϵ�����ж������ԣ����Ծܾ���������������ڰ��ֵ��Ƕ��������۵����£��Ͳ��ɶ��Ƶ�������Щ����˼�档
��������Ȼ�ǵ���Щ̸Ц�����������ʱ������δ��й�ƫ���뼤�飬����һЩ��������ֹ�����ª�����������Լ��������������������һ�棬�õ����Ķ�����������Ұ�ľ��ޡ���Щ��Խ���µ��������ж��Ļ�ʯ����������Ը�����̥���ˣ��������켺����խ�ӵ��ﴩ�Σ���ƾ����Щ���Σ��߳��Լ���·�ߡ�
������������ʮ�꣬�ڹ������ٵ�ĩ�ջ����ǰ��õ���һ�С���л���齫��Ͷ���Ⲣ�Ƕ�õ�ʱ�����Ҽ���ij��ӵ�й�ͬ�������֯��ӵ����һ�ָ�С�������ܵ�˽�˹�ϵ��ʮ��Ŀ��Ⱥ�����û�ж�ȥ�ң���Ϊ����ҵ�������δʹ���ڤ�����궮�ú�ν��ȷ������Ҳ��������������
��������������ʱ��̸���룬��ʱһ�����У�������Ը��������й������հļ�����ս��δ��ʱ���ø���Ư�����������ġ���������Ҫ���ˣ���������ҫ������������롣������Щ�к�ʱ�Ҳ�֪�������������ö����㡣
�������������߹�һȦ֮����һ�����У�ֻ���Լǵú�ֿ�ѵ�Լ����������Ҫ��Զ���ᡣ����˵���������������ˡ��������ڵ���˹�ٵĿ�Ϯ������δ�������������εĵײ���������ȫ����������˭Ҳû�ж�ƽӹ��Э��
��������ֱ�����Ͻʼܵ���һ����Ҳ��˵����������������߹���ȫ�����¡������ҵ�ʢ�꣬���ּ����˵۹������������ǵ��껪�����е���������
����1948��5��15��17��
��������
������ԭ�ġ�
�����Ұ�����Ѷ��ġ����бʼǡ����ϣ����������ߵ�����ҡ�ȥ��ʮ�����Ȿ��ĵ���������ڰ����ȥ���ҿ���̸̸�����ļ��⡣
�����������Ȿ��������ķ��ɴ��ߵ���Ʒ���ᵽ������Ѷ��Ǿ����֣��ɴ�¹�ʱ�ڹ����������֡�������ע����Ա�����ڳַ��ɴ���ⱻ����̫����������1945��4����������������д�������飬���о����Ȿɢ�������ż��������ΰ�ȫ��������ֵ�����٣�����Ѷ���Ҳ���ҵľ�ʶ������֮������ʵ������1943�����������밲ȫ�ֵ���ϵ������
������������ù������е�������ʱ������ƽ��������������Լ���������Ҳ�����������ԡ��������Ǽ�Ƨª����������˼������������һϯ��������������ң���һЩ��¶���˵����¡��������Ҫ����Ȼ������������Ҫ������ʩ�������µ�������������ʥ��˵����ѧ���ҵ��ͷ���������ʩ�����滻Ϊʩ���ߣ����ǵļ����һ���ˡ��������Ե�ֻ�ǵ�ǰ��ִ��������
��������Щ�Ȼ�ؿ����ң��·���»���߲�Ӧ����־�����Ĺ��š��ҵĸ�����һλ��ؽ����������½�ͽ���Ҷ���ʱҲ���Լ���ѧ���ο�����Ϊ����־�ˣ�����������ľ���
��������Ѷ�����һ��������ɵ�ʱ���д������Ӧ�������������ԡ���������Ϊǣ����һ��Ӣ�����������ȥ�����˷��ԣ����ġ����бʼǡ����ɴ�ʱ�������١����������ɱ��ʱ���Ѿ���ȥ������������������������ҵ����Ѱ���ĸ�ͬ��������������ĵ��ң���������֪��Ѫծ�̴档
���������������Ҫ����ֻ��Ҫ��רҵ��������Ȩ����������Ȩ�������ҵ����Ѳ���ϲ������Ѷ����������壬���Թ��ұ߽�������Ϊ��Į�������۵�����ͬ������Ҳ��ȷ���Ȿ����õ���һ���º͵�����
���������ҵ����Ѵ��ż�����Ϊ��ָ��һ�������ĵ�·���������ߵ��������ľ�ͷ������֪��һλ�������߸�˹���������á���������ѧʱ�Ĵºţ����ڡ������Ƕ����������Ѿ����ڡ������ǿ���̸Щ���õĻ��⡣
����1948��6��1��
����������ע��
��������1964����������ʱ���ᵽ����λ���ѣ���ʱ����Ϊ���������ڷ����Լ��ļ������������ɭ˹̹���Ǽ����Ĵ�ѧͬѧ��������ʿ�����ڵ¹���ս��ȡ�÷��������������ڰ���һͬ�ȹ�Ԣ����������£����ڵ·��߾��Ͻ������ţ���������һ���š���1956�꣬�������˼�����ͼ�ո����µ��dz���ı���°ܺ����������������ɭ˹̹�����Լ��ĵ�λ������������ߴ����˼�������������ڶȼٵķ�����Ŀǰ��û�з��֡�
��������һЩ������¶�Ļ�Ե���ҵ��������������λ���ѡ���48����ıʷ����Բ�һ���ˡ�������̽����
��������С����Խ��������������ǡ�
����1947�����ɭ˹̹���һ������Ѷ��ġ����бʼǡ��������У���Ϊ���뱾������ֶ�ƽӹ����Ч������������������������š����Ҹ������������Ͷ����CIA������������Ϊȱ������OSS�ĺ�̡���������������ɳ�������������֮�˵���������ֻ����üʱ��¶��Ӧ�е�����������˹�ƶ�����������ȥ����������ʧ�ٵ����վ�Ϥ���������ҽ���������Ĺŵ��ﰲ�����Ľ�������
������Ϊʲô����
����������������Ѿ���Ϊ�����Ĺ�Ӷ����ǰ�¹�½���ܲ�ı����Ҫ��Ϊ�������ʣ�������������������֪�¹��������Ū�������ã���Щ�߹����г��գ���ʮ��ս��������ʼ��˹�ƶ�����ȴû��ǰ��������˾��ϵ�����Ӣ�����ɼ����ⳡ��Ϸ���ȫ����������һö���ӡ�����ɭ˹̹��Ļ����������·��������⣬��������ҿ������ߺͼ��ֻ��һ��֮���
���������Ҹ���ǡǡ������������Ρ���
��������ֹ��ˣ��������˸����Ƽ�������ɳ��������˸���ϵ����ƣ�������ƫ���⡣ʩ�ױ�һ������ŷ�����ϣ�������ʵΪһλ����־���������ߡ���ϧ�첻����Ը����ʷ��Ȼ�ص���1618�꣬��Ϊ��ս���ĵĵ¹���һ�ε����ܺ��ߣ��ⳡս������������չ�������������Ӳ�������
������ô��������������1947��ף�����������λ���ѻ�֪��һЩ�ⲿ�������������ĵ۹��������һ����ʵ��ս�����������ǵ¹����鱨�٣����Ȿ��Ȼ�ᱻ������������ıʼ������ʼ������ȫ�������Ͷ����������������в��Щ�����������ˡ�����ʱ��ʼ���Ȿ�ʼǾͲ�����һ������֮�˵������ʰף����������ޡ�αװ����̽��ҪЮ��Ŀ�ꡣ
���������֮·���ϣ�
����������ע��
��������ƪ���½���ǰ��ȫ�ֹ������δ�����������Ա����ģ��������ɴ�¹���һ���鱨��Ա��ս���ﷸ���ֱ�Ϊ���������鱨�֣�CIA����Ա�Ĺ��̡����ڡ����бʼǡ���ƪ����ڤ������������ľ������������ͬ��������ˣ�ȴ���ڱ�ڵ�·�ϡ���һ����������������������������ʷһ����
�����ͼ���Щ���ֻ����Ҳ���ʱ�䡣����ɢ���ڱʼǵ����ҳ�룬ʱ���ʲ��ѱ棬ʱ��ǰ���Σ��ƺ����������¼���ǣ�ȴ��Ը����һĿ��Ȼ���������ǹ�ͬ��ѭһ��������������˵����������ˣ������⼸ʮ�β��ʼ�¼�Ķ�����Ա༭���ġ�
�������϶���������Ը��������˵ģ�����²���Ҳ�������ߵ���Ը�����Ǻ��������������Ϊ�ܿ�֪ǰ�˵�˼�����ҽ�֮�����ģ������С��ұ��˽ڣ���������֮·����Ҳ�����Ǹ�������ׯ�����ĵ����ꡱ����Ϊ�⣬�ַ�Ϊ��ƪ��
������ƪ���ɴ�ʱ��һͬ�սᣬ���µ����˹���Ϊս������ƪ����1948�꣬����ս����Ϊս�����˿����̽������֣���ƪ����֮�����������ͱ��һͬ���ã���קס����������������������ʵǵ����������ĵط���
��������һ������ĵ�·�����������������Խ�����˵�ʬ��������������ʤ���ķ�ʽ���ھ���֮ս�ս�ĵط���ֻ����������������
��������������������ˣ���������̾�����������۶������ֿ������ڸ������ʱ�����Ÿ�����������壬����ijЩʱ������������ֻ���������ۣ����κ��˶�����ˡ�ֻ���е��˲���ô̹Ȼ���ܣ����Ϊ�������ж���˺��ʹ����֡�
������ԭ�ġ�
����������Ҵ�1945��3�µ��¹�����ǰ�ľ���д��������Щ���Dz�����˵ġ�
�������Ƿ���սʧ�ܺ���������Խ������ӣ������ƽ�������ƽԭ����˭�Ƴ������Ǹ���ϵ��Ȩ�����������Ĵ����⡣
�����DZ���45�����������һ��ǰ��ɭ��½����Ӫ�������غ�ը��Ԫ˧�Ⱥ�������㣨�ܲξ����Ʒ����еı�־��������ע���ص������մ�֣������ɴ����۽�ʣ���������ս�Բ���
������ʱ�������������ɸ������Ѿ��ɹ�����ӣ���������ŷ����һ���ӵ�������˹������ս�ߣ��¹��д�ı�������������һҹ֮�䣬ŷ����Խ��½����ı��ɥʧ����ԣ������ڹⴰ���Ļ�������ֻ�з������������ۡ�
������Ϊ��ȫ�������붫��������������ˣ��Ҽ����ϯ�ܲεĻ��顣�����˶���������ͧ����ô����ͳһ���𣿡����������ߵ�������˵����������С��ȱ���������۾������ڻ����
����������أ������ٽ��Ƕ���������������ŵ��ﰲ��װ�ײ�������ս����ʼ�ˣ�720�¼������½���ܲ�ı����������ע���Ķ�Ŀ�������Ŵ��µĽ��ټ��£�M40��ľ�װ���ɡ�ͨ����ֻ���ܲ�ı������ʱ�ṩһЩ�鱨��������ȴ����վ��������������ߵIJ�ı��Ը��ͽ���һЩϸ�����⣬��������������������ɵĺӣ��ҽ���ʤ�м�����
�����������棬һ������Բ���۾�������ʮ��ľ��ٽ��˻������±���ķ��ǰ��������ķ����
�������Ҽǵá��������ǰ�����������ڲ����������������������׳�������������
��������������
�������������ҵ���֪�������߾��������
������������ĵ��ֶ�ķ˹һ�����������Ҳ������ɺӣ���������ս�����ڳ���չ������
������������ǰ���������ݡ���
�������ǵġ�����
����������������Լ�¶�����˶��������鱨�ٵĻỰ���������������Ѿ�����һ��������˼·����Ҫ���ǣ���˵��������
��������Ȼ��˼ά�����������û��˵����ս�Բ�������ս�־ֳ�Լ�¶��İ壬������������Dz�ı�����鱨�������м��⣬ֻ�����ṩ��Ϣ�ķ�ʽ����ʾ��������Լ�¶����ְ�Ŀ��������ı����˹ŵ��ﰲ�����ú�ֻ˵�����¹ٶ�ս�Բ�û��ʲô�����ļ��⣬ֻ�dz��ڶ�����ͬ�еĹ��ġ���
����������½���鱨ϵͳ��ȭȭ֮�Ŀɼ�����ҲҪ�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