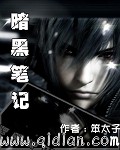���бʼ� by ��������-��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ļ��⣬ֻ�dz��ڶ�����ͬ�еĹ��ġ���
����������½���鱨ϵͳ��ȭȭ֮�Ŀɼ�����ҲҪ�չ˱���Ϊ�����ҵ���Ըѽ����Լ�¶���Ц������
�����������������Ⱥ��ĩβ����ѹ�͵�ɤ���չ������������������Ҳ�����ˡ���
����������������Ŀ�ꣿ��
�����������죬����һ�������Ц�ݡ�
��������������Խ����ɽ��û��ֱ��ͻ������ӣ���������������ͷ�����������ٹ����������ݱ��ϵĵ��߾�������ģ��±���ķһ����ϡ�һ��֮�����ҵĹ��編���˸������ҵ���˼·�ص����죺
����������ú��������������졢����֮�����������ڿ����ڶ���У��ǵ¹�����ĵط���
��������������������Ҫ���֡�������ң��Ͱѵ�һ���ž������߳�������ŵ����ߡ�������ֱ��������ķ������š�
������һ���ž����������ߵĶ������������������ڶ�Ӣ�����š�������ʲô��
�������������¶�������Ҽ���˵����
������������Ѱζ��Ŀ������ң����Ҳ����ף���װɵ��ʲô�ô�����
�����ⷬ�����Ѿ����ٳ�Ϊ���ܵIJ��ϣ�Լ�¶������Լ����ܵ������پ��ӣ��ŵ��ﰲ����ı��һ����ƣ��������������Ͷ���������뷨�ǣ����������Ӣ�������շ����ĺͰͷ����dz�������֮ǰ���ֿ�ס�����Բ����DZ��Ľ�������
������˵�ú�ί������Ȼ�Ǹ�����Ȩ����˭�����⡣
����������ͻ�ȥ�ˣ���������ȥ�Ķ���������ͨ������������ȹս�ͣ�������ó����еĹ��У�������ȥ������֣��������Ӧ�û������Ϯ��һ����ɾ���˵�ˡ���
��������45������ʩ�ױ�һֱ��������ֵ��⽻�����Ѱ����Ӣ�����⽻̸�л��ᡣ�Ҷ��������㱨��������Ѿ����Ѽ������ˡ���������Ҽ���Ӳ����������ˣ����ȴ����¹������Լ��ij��롣
������һ�ֲ��ɾ�ҩ���������塱����仰ԭ�������ҵġ�
�������ײ�Ը��ʩ�ױ���Ю�ƣ���Ҫ��ıһ�������صĵ�·������·��Ҳ�����ң����ǻ���һ��������·��һ����֪������û�л���������ˡ�
��������λ�ﻹ��һЩ��Ҫ�Ҵ����������������ҵ�����������𣿡������߶���ѡ��
���������ڱ�������ֵ�һ�Ź����Խ���ǰͣ��������ɫ����ǽ����ʽ��ͨ�Ĵ��Ž������ν������˿������һ�����������Һ�һ���ܲ���ξ���˽�ȥ�����Ǹ�������ȷ���ҵ����ٵġ�
�������������Ǻɶ�ʩ̩���ˣ���ĵط����˺������������ᶨ���ֻ������������˵������Ϊ���������ŵĶ����ɾ������һ���˼��б����˵����£������Ϸ����������ڽ��ʣ�����������յ����ĺ��ۡ�
�������Ҽ��������ˡ�����̸������ʱ����ʶ��̧�����������Ǻ���ͬ�˵ľɶ���ש��ɫ�ķ��������˺��̿������˾�������Ͷ�µ�һöը����
������ս��������Ҳ���ᱻӢ���йܰɣ�����Ӣ���������������������ڿտ��Ĺ�������յķ��ž���һ����Ĺ�ҡ�
�����������ôʾ䣬��Ԫ�ײ���˵����Ҫս��һ��һ�䣿��
��������ô��һ��һ��úúõ��룬����α����Ӱ�����˹�������������ҡ���
�����������������ҡ��������һ��֤�ݣ��պ�����ռ���߾�����������������ֳ�Ϊ��֤��������һ�����������ܵĵط����������Ǹ�����Բ���۾������ˣ��������ҵ��ų���������ʱ�����ǹ��ij�·Զʤ����Ǩ��
�������ҷ������������㶫�������Ҷ���˵��
�������õģ��õġ�������Ȼ�ó�Կ�ס�
����������Ϳ����°ࡣ���������˾���𣬾�˵������ȥ�������´��78�ţ�ȡһ����Ƥ�顣��������仰ͣ��Ƭ�̣�����������Ҳ�Ѿ��°��ˡ���
�������õģ��õġ������ٴ�Ӧ�е���æ���������˳�ȥ��
�����ָ��º��ֽ���ڻ�����ӱ�Ե��ʼ���ڣ�������û�ڲн����С���Щ���������Ź��������鱨���Ĺ��������ɵ۹���ȫ�־ֳ�������ϣ���ⴴ����1939��ʩ�ױ������������¼���������ŷ��һ���ĵ���������ʱ�������ȥ6�꣬�������Ѳ��ش��ڡ�
�����Ұ�һЩ���Ų�ͬ��ɫ�ĵ����г������ÿһ��ֻ������Ҫ���¹���������ս�ɵ�Ӣ����ͷ�˰�˹����1939��11�±�������ɯ������ϣ���յ���ϵ��40��ǣ��һ�ߣ���������ĺ�ɫ�ֶ�ȫ����û���������ڲ��ѱ䣬˹���ָ���Χ��սʧ�ܺ���ס�������dz�Ϊ�¹�̽�Ӷ�����²����ɫ�ֶ���1944��2���������һͬ��̨���˺�ֱ��ս���������¹��������ĺͽ������鴦���档������Щ�����Ѿ�����Ҫ���ǣ����ý�������˵��
��������Щ�����漰�ִ��¹�����Ч�ʵĵ���ϵͳ��������������Щ����վ����ؼ�������˭���鱨ϵͳ�ǹ��ҵĶ�Ŀ�����ߣ�������������֣��¹��ͻᱻ������ͷ��
�����������������Ӱ�����˹��������������ô���ҿ����ڵ�����ս�����Ұ�һ�����ڷŵ���ξ���
��������Щ��������Щ����û�и��������Ͼ��ȵĻҳ���ʾ����δ���˷�����д���ܶ��˶���������ʷ�����ǵ���ʷ����һ���ּ仯Ϊ���У������ֵ����ˡ�
�������������룬��������µ�ʲô���պ��ܻ����á���
�������˾�����ϣ���¹��������ڡ���
��������ô����Ҫ������
�������Ȼ��ֹ���������Լ��Ƿ���Խ��Ӧ�еľ��롣�ҵ�Ȼ�����ȥ������֪������Щʵ�齫��Ϊ�¹��鱨ϵͳ���½��������ݣ�������֮ǰ���߲��ǻ�͵ȡ�Է��ĵ��ơ�����淢���̰����ˡ��ٻ�ʬ�����Զ�����˧���ȵ������䶨��ʤ���߲���������Щ�Ҵ����˵ġ�������
�����Ҹ�վ���ıߣ��ҵ���˾ʩ�ױ��Ѿ���������ϵ����û�и������ε��ϼ���
�����������ɲ�̫�ó�������������ֻ�Ǹ�ר�ҡ�����һ�ʴ�������ξ̫���ᣬ��Ϊ���һ�������ͨ������������Ը�ټ���ʱ���һ�û������ʾ�ڡ���
������Ϯ��������ʱ�������Ѿ��ڵ����ҳ��̡������������ױ����أ�������У���������鴦�Ļ�Ҫ������ֻ����ÿ�ݾ��ڵ���Ҫ���������̲�����Сʱ������û�����鴦�İ��������ľ����鱨ϵͳ��ս�����߶�Զ�������ҿ���˯���þ��������˾���Ͷ�����ˡ�
������������չ���ʮ��������ɫ���۾��ɾ�����ʹ���ʱҲ���º͡����ȵ�ս�������������������ʱ�������ڲ�Ҫ������������ˮ�����
������ǰ���˸���˵�����ƵĻ���Ϊ����������ʹ�ļ��ס���û�����Ǹ��˶���������ƪ�������������Ǻܴ����ģ����������е����ء�
����1948��6��3�ա�6��5��
��������ƪ�꣩
���������֮·���У�
������ԭ�ġ�
��������1944��4���߽������߾�λ�ڴ�Ľ˹���ص�ս��Ӫ�������Ʋ���ͬ������ּ��ռ��¹����ϺͰͷ����ǣ�ƾ���䷢�﹤ҵ���������붫�����ݣ���û�б��ϰ��֡�
����ս��Ӫ�Dzֿ�Ľ��ģ�������ʿ���ڻ���ͷ�¶�ޡ������ȱ������ǼǴ���һ��������У���ժ�����ɽ�����ļ��£���̫�˳ƽ����Ƶĵ����������Ĺ�������µ��˰ѵǼDZ�����ϥ�����Լ��Ȼ�����ֿ⡣ξ�پͱ�����ʿ���Դ��ˡ�
����һ��У���ڽ�����ʱָ��ָ��������Ȼձ꣬��Ӣ��˵���������Ǹ�ҽ����doctor�������в�ʿ��doctor��ͷ�Ρ����ܷ�Ϊ�Ұ��ŵ��˼䣿��
������û�Ŷ�����Ѿ�϶��Ǹ��ɹŴ��Ȼ�����Ҹ�����Ǽǹٰ��������ˣ������¹�У�ٺ�Ц��һ�š�
��������һЩ�ڻ����ݣ�ij��֪���������Ĺ���ʦ���鱤��ѧͼ��ݹ���Ա���������ܲ���ξ�����������ϵ��������������档�һ���������װ���������Ҵ��˵������Ʒ���������ѹ����ɫ�ı���ɫ����������������Ͷ������������
������������װ�������澯����У����ģ������������۹���ȫ�ֹ��������鱨���������������������ϵ����ݡ�
��������ץ��һ������̫����������������ͬ�Ŵ��ұ����ɷ�˵������������
�������Ҳ������ܾ��졣��
��������ղž�˵�Լ��Ǿ��죡��
����Ҳ�������������о��춼�����ܾ��졣
��������û��������ʩ����Ա�ܼ����߲��ܿ����ӣ�������ʳ��ȱ�ͷ��ص��ͽ̣��˿ڱ㡰��Ȼ���١��ˡ�������ʹ�����ɴ������Ӫ����̫���۵Ĵʻ㡪������ע��
������Լ����һ���£����ٱ����ճ����ߣ�������Ϊ���µ��˽����������������������ڸ�����̸���ˡ����Ҷ�һЩ�Ϻ���������ƾ�˵����У��˵����Щְҵ�������и߰������Ҷ���ѧʱ��֮�����öࡣ
���������������������ȴ���ֵ�ƾ�Լ���ʵ�֡��Ҷ�����һ��������ϣ������Ϣ�����ҵ���˾ʩ�ױ��Ƿ��Ѿ�����Ӣ�����Ƿ��Ի�ӻ��ң�����̯�����ƣ�Ҳ���ᱻ�������Լ��˶��ߡ���������˼��ȥ���ʱ��
�����ܿ��Ҿ�֪������뷨��ô���档��Щ�����ߵľ����DZ�����Ϊս�����������������̫����Ҳ�������С�
�����ұ������������Ӫ��������������������֣�������������Ӿ���������ϣ���ճ������ͨʿ����������Ŀ���ȵ����б��д����̡���Ϊ�Dz�ս��Ա������Ϊɿ�����Ƿ���ս���ٻ����
�����ܲ�ı���ŵ��ﰲ��δ��Ϊ���������������������֪���ġ�
�������ͬʱ���˹��ķ����ֵ�Ŧ�ױ�����������21���۹���Ҫ��ս���ͷ��˵������������Ե۹����ص�����ҪԱ���Լ����е�ֱ��ִ���ߣ����������������֡�����˹����ĵڶ��꣬�ұ���֪����Ϊ�۵�֤�˳�ϯ�⽻�����С�
������ϴ�����棬��������������ʽ���ա�Ŧ�ױ��ĵ�·����������й����絳��ȫ�����ᣬ�䲼��������̫�˵ķ�����й��۹������̡�һ������Ǻ���վ����������յ���ͽ��������Ĺ����
�����˾���ͥλ��һ�������εĽ����������������һ����ͨ��С�ķ��ӡ����������ϻ����Ž���ı��棬�⽻�������˹�أ��룿κ����ˡ���ֻ��������λ��ѧ��˾������ѧ�Ķ��ӡ�������С���꣬���ҽ���ʱ��˵���ҵļ������Է��������ࡱ����������˽��ȫ����Ϣ�����飿�룿κ�����ʵ�ʾͶ��ڷ���˾�����ѧ��������ע����
�������ȵ�һ�DZ����Ǽ�¾ɶ���������ķ�ͥ������ý�����ƴ�Ŀ������ϯ����ı���̨��վ��һ�����ݵ��ˣ�����ȥ�챻������û�ˡ�
������ʱ�Ҳ�֪������Ҫָ֤�����ҵ�ֱ����˾ʩ�ױ�����û������Ӣ��������������������һ������ָ��ɿ��ս���ͷ��˵�������������
���������Ǻ���ģ����������ϵ۷����ҽ�ֱ����ʵ������վ��֤��ϯ�ϣ��������������
�����߶��أ�ʩ�ױ�������¹��ڷ����������ڼ������˽���Ӣ���������������¼���1941�������������ֹ��������鱨�����꿪ʼı��ͨ���⽻;������ս���İ취��ս��ĩ�ڣ�������ϣ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