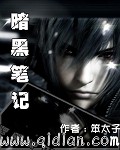���бʼ� by ��������-��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Ǽ��ڱ������ҹ۵�ʹ����Ϊ����������鱨Ա����������Ҳʹ������������鱨�ߡ�
����������ȷ���ʺϵ�һ������ѧ�ߣ���ѧʶ��������������������š����鱨Ա��������û�������Ļ�ɫ�ش��ģ�Ψ�˲����Ѽ��������Ϣ����һ�㲻�����������ߡ���
�������µ�ʱ�������ձ�õͳ���ή�ң���������ս�������̵�ʿ��һ����Ȼ����������ظ����Գ������Գ�����ŦԼ������ֱ��ս��ĩ�ڲŸ����������˵¹�����������֮�⣬���������û���κ���ϵ���һر��Լ�����˵����
������������һ���ԵȵĽ�̸��
�������������Ϊ����������ұ�ͬ���Ǹ���ʤ���鱨�Ѽ����������Ǿ�����һ����ʵ���ж����Ҳ��ò����ϣ��Ҷ����������֪���٣�����ʱʱ�е����������С���
�������˵�֪ʶ�����Ǻ��ѶԸ��ġ��Ҹ������鱨�������Ը�ֵ��ֱ����أ��������Ĺ����ߵ���꣬���Ƿ���������ȴ�漰������
������Ҳ�����ǶԵġ��ҵ�ȷӦ�þ���ص������������ұ�����ѧ������������ÿһ�춼��˼����硣��������˵������ȫ�����Լ������磬������ͦ��ֵİɣ�һ����̫�˶��´�½��˼��֮�顣��
��������������ľ�¡��ϵij������Ҫ��������öࡣ
�������漴ӿ������������
�������ҵ����IJ��������ڲɷ����ǡ�������ʱ��û�������ɷü�¼���Ϊ�о����ϡ����Ƿ�Ҳ��һ�ֲ���ʵ����
��������һ����ƭ��
������Щ����Ĺ��������Ȼ�������Լ������б����˰��ᣬ������һ��һ�Ľ�̸ʱδ�������⣬����Ȼ����ƭ���ҿ���������һ�ԣ�ֱ����¶����ڵ����顣
��������������Ҫд�����顣��ס��ƭ��Ʒ���أ���ֻ��ų�������������
�������ǽ���8�¼�����ˡ��ֹ���һ���£��������ؼĸ���һ���š�
������������
����Ҳ�����Ѿ�ͨ�����;��֪����Ŧ�ױ����нӽ�β�����������һ�ص�������Ͷ��ѧ���о����С�
�����������������������ڱ˴˲�δ��ͨ������£����Ҹ��˵���������ȥ�����ɴ���Ҫ�ġ����������ѧ���Ƕȿ�������ǧ���˾������ѵ����壬δ����ʧ���Ρ��������漰�������IJ��ģ���Ȩ�Ѿ����һ���˵Ĵ��ˡ�
������������ս��ĩ��Ͷ�������ԭ�������ų�����һ��ͬ����ֿ��ԭ�����ڴ�ѧ��ҵ��Ͷ�������ӣ�����һ��������֮����½�������ԡ�
������������������ʱ����˵���Լ�����ʵĿ�ģ�����ų���ģ���Ҳ����Ϊ�Һ����ǵĹ�ע��˲�ͬ����������ҵ����塢���������ĺϷ��ԡ��������������ɡ���ȥ�ļȳ���ʵ��δ���������ܣ��ҹ�ע���Ǻ��ߡ�
����������Խ�������Щ̸����������ѧ�Ƕȷ����ɴ��30��40����¹����������������һЩ���Dz����ģ�����Ҳ������֮��Ϊ���������ڵ���һЩ���ؿ���ƿ��
������Ϊ�������սʤ���ҹ��������硣��л���Ƕ��ݵġ���˽�˵Ľ�̸������������˼ά���������ݣ������ҿ�ʼ��ע�����������硣�¹�ֻ����ʷ��һ�澵�ӣ��ռ������˵���֪��
������ֿϣ���ϲ��ܸ��������������������Ϊ�������ɾ��ౡ֮�⣬���������ĸ�ο��
��������ϵģ�
������˹����������
�������Ǹ��ѷ�����ģ�����������ǰ�۲��Ҷ���ʱ����ɫ�仯����������������һ�����������ĺͲ������ķ�ͥ����֮���ұ�ø��ױ�������ο�衣������Ц������Զ�ȼ����������������Լ���Ŀ�ġ�
������û�л�Ӧ��
���������Ը���ļ�Ӳ�Ƿ���Զ����Ƶľܾ��������÷������仰��ɵ��
���������Զ�Ī�����ƵĽ��ġ�
��������ҽ����ο���������ϵ�ȱʧ������ѧ����ֻ�ǽ����������ѷ���������˰�˹������ҽ����������������������顣������ÿ��̽�ö����ˡ�
�������º͵�Ц�ţ�������١�����ҽ����ְ��֮����ҲԸ�һ����ͨ�����ڡ�˵��ģ���������ô���ƫ��֮������������Ĭ�������ҵ���ö����ﲻ̫�ࡣ��
�������е����ã�����������ǰ����һ���Ͽҵ����ӣ�����ʽӢ����������������������������
�����ж����˶Ը��ѷ̻¶����������ͼ������λ����ѧ�ҵıʼǣ�����һЩ��ͥ�ϰٿ�Ī����Գ������ⲻ������Ŀ�ġ����������ƣ������������ÿ�����⡣
����������һֱ����Ȧ�ӣ����Ҷ���˵���������ѻ��ֻ����ԶԷ�ΪĿ�꣬ʲôʱ����ֳܷ�ʤ������
������Ц�ŵ��ͷ���������ǽ���̫�أ����������ģ���û��ǹ��ֻ����������
����Ϊ͵����ɱ���
������һ���˲��ܼ���������ǰ���ּ�װ����������������˵�Ի������ô����Բʷ����ٰ���һ����֦���С�������˵������ǻ����������Ҳû���Ծӽ̵����ζ��������˵���Сѧ����ϰ�ߣ��ܹ�����Щ����С�ʼDZ�������ǰ���ϲ�����
�������ҵ��ܲ���̫���أ������������ոչ�����һ����������������ȡ�����ָ��������ҽ�������ݣ������������δ�������κ�һ�����˿���ҩ����������ʲô��������������Į��ҽ������
���������Ͱ��Ц����������ʾ���̸������Ȥ��
����������һ��ְҵ��������Ƿ������������̽�Է������ܣ���
����������һλ�Ѳ��˵���С�����ҽ������Ϊ�β�ȥ��˹��������
����̸�������ˡ�������Ϊ�ζ��Ҹ���Ȥ���������еļ����������������Ȼǰ���������ʺ��Լ��ü�������ʧ���ˡ����ɼ�����ȷ�������ijɰܡ�����Ц������һ���˻���Ϊʲô˵Ļ�������Լ�������Ҳ����Ц�ˣ���ά��˼·���ݡ�
�������������ڼ�ȥ��ʲô�ط���������Щ�ˣ�Ŧ�ױ��ľͳ����ˡ���
���������ܾ��춼��������Ѷ�ӷ��ģ���
��������ʹ������ʨ�ӣ�ż��Ҳ��ɽ�������֡���
������̸̸����ô�Ը�����
�����������Լ�����һ��С���٣���̸����͵͵���Ի��������
��������ƣ���ɲ����档��
����������һ������¶�����Ͳ����ˡ���
��������һ���ó�ͷ�������ٳ��ӵ�ũ����ֻ���ʡ�
�����������ץ���ܴ��������̫����������
����������δ���ܱ��ڿ������Ⱥ������µ�ͬ־����
������˵�����Ǹ����С˵�����ߣ��������������������������һλ������Ϊ���桢���Ȱ������Լ��Ĵ����ɨ�ּ�����������ܲ��ܱ��������⸱�����۵�ѧ�����ӡ�
�����������ֱ������һ��б�İ��š��������һ���������
������ף������֮ǰ�ҵ��������IJ��ˡ���
�������������ڱʼ���д�����˾ܾ���̸����Ϊ���һ�仰��
����1946��9��15��18��
����������ע��
������˹������������Ŧ�ױ������䱸������ѧ�Һͷ��롣�����ڼ�������ÿ�춼�뱻������һ���������ǹ�Ȼ��˽�µ����ۡ�������ġ�Ŧ�ױ��ռǡ���Ϊ���ʱ��ļ�֤��
�������������ѷ����һλ����ҽ������������̸��Ŧ�ױ������������Ӻյı��棬������һЩͬ�����ɴ��������Ӹ�ְ��֤�˵����ۣ�������ʩ̹������ϣ����³��ȡ�������������ʹ���ָ彻��һλ��ʷѧ�ұ�Ϊ��Ŧ�ױ���̸����
�������Ѳ²����ǶԱ������ߵ���Ȥ���Ժη������ǵ���ҳ��Ϊ��ЩԶΪ��Ҫ����������ģ���������ֻ��עŦ�ױ���22λ���棬���ѷ����ҰҲֻ�Լ���Ϊ֤�˳�ϯ��һЩ����������Ǹ��ֻ�Ӱ�������������Ŧ�ױ�������û���κν�ɫ�����⣬���ѷ��1946��7�¼��ѻع�����������9�³�������˹�����Ƿ�ר�̵��ã�
������Щ�����Ѿ��������ˣ�̸���ľ�������Ҳδ�����ء�Ϊ����Ϊ���ߺ����ߵ����Ƕ���������λҽ������������ΪһЩ����ʾ�����Dz��dz��ڶԼ����������ɴ�ʱ�ڵĹ��ε���Ȥ�������ġ�����һ������ͨ����δ����ʷ���صĽ��䡣
����1961�꣬�������ؽ���Ŧ�ױ��ռǡ�ȫ��������ͬ����ѷ��������ಡ��ǰ����̫���ͼ���Ӫ�����˰�ϣ��������һ�걻��������Щ�¼����ǹ����������������غ��ѷ����˹����Ѱ����ʲô�����ǹ�ͬ��������һ��δ����¼����ʷ�����ڱ������Ľ��컹����̹�ԡ�ʱ��ᵭ����Щ����Ӣ�ۣ�������ĵ����ջ���������Ȼ���ҡ�
�������֯����
������ԭ�ġ�
�������ߴӴ������������������IJ��á��ҵ����ҵĴ����ܹ������ٳ�һ�������Ľ��̼ܡ�������ǽ�������Ա�ȡ�ø��ȹ̵����У��������ݶ�ƽ��ĸ߶��㹻�����κ����͵�ŷ�ް��ˣ�����һ�������ڽ��̼����ڻ��⣬�����Dz����̵ġ�ֻ����õ�����������ڿҵ��ո����Ĺ�ʵ�������ǵ������֣�����ʦæ�ż���̾ߵĸ����豸��������ȥ����ͽ����ָ������ǰ��һ�о�Ȼ����
������Щ�����Ѿ�����˹����������С���꣬�ظ������棬ÿ���Ҷ�����ȥ����ֻ�DZ���ȥ����
�������ģ�̤��Ļ�Ȼ����������ʱ��ҡ�ε�ʬ�廮���ķ������ս�ʱ��Ħ�������������Ͻʼ�ʱ�ĽŲ������еļᶨ���е���dz��һ���еIJ������ң��е��DZ�����ȥ�ġ�������ø����������Ա�����������ĸ�Żʱ�������ŵ�˵����������������
�������ǹ�ע�����ֳ����ⲻ����һ����ữ����Ϊ��������ʹ���ǹ���һЩ�н����������⣺���������������սᣬ����ֻ��������Щ���ܻ��ζ���ѧ������ľ��������������ڱ����볬��֮��ģ��ɱ���ر���ʵ˺�÷��飬��һ���ܾ���ˣ���ֻʣ�±��У��Լ�˼��ı��С�
���������������ڱ����У�Ҳ��������С����۴���ʲô��ţ����ȵ�������������ƶȻ����뱩�����죬���������Ȼʵ�ֵ������ͬ�ڱ�ͽ�����������ڴˣ������Ϊ��ʹ����Ϊ������ϵ���Σ�����ȴת�����ˣ���Ȼ��ʡ�
������Ҳ���Կ������С����������ҵ����ݣ�������ͳ���߸����������������˶��Կ������У�������������ĩ��������ɥ������ʵ��������һ�γ�������ʷ����������Ȩ�������ѱ��Ƴ������Եļ�Ȩ��δ�սᡣ
�������������������Ե����¡��˿�������������������ĸ�ҥ������֮�������������һö��ʿѫ�£�а���������ʾ���ʰ�������������ô�¾ɣ�ʮ����ǰ�ɴ������ս�κ�꣬��������Ķ����������һ�����塣
�������ǽ��̼ܵڼ�������ת��������н�չ���٣�Ŧ�ױ���ͥǰ�İ��������Ѿ����̶��ˣ��Ӽ���Ӫ�Ĺ����ߵ����������ӵ����꣬���Ƕ�����У�١�ξ�پ��Σ�ֻ�ڵ������ϼ���Ԫ�ף�����ֱ����ǰ�������۹��ĸ����������Ϊ��;ĩ·��Ϊ��������������һ�أ���������˾�ߵ��磬�ڵ����۹��ľ��߲��Ƿ�������δ����ʱ�����Ⱥ��������ге�����
����ս����������ȥ����ս���ԵIJ��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