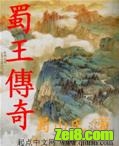ƽ����-��19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ô����֮����ɻ���ɲ����ó�����һ����ٶȷɳ۶����������ƶ����������ǰ�����������������ǹ��ƾ���⼱�ٵij�������������ķ�â�����˱��������Ĺپ��������ϣ�������ȫ����ס��˷�â��
������ǹֱ�Ӷ������˵��ؿڣ���Ѫ�ڷ����зɽ���˵ʱ�����ǿ죬�����͵����ڱ�����ͬ�ڵ�������ǽһ����ֱ�ӹ���پ���Ӫ��ǰ�涪����ǹ���˰γ�����������������û��ʲô����������ƴɱ��һ��������һ��������������ʿ�㲻���پ��Ĺ������پ�Ҳ�����мܻӿ������ĵ��档
��������û��ֹͣ�����������ϵ�Ѫ��쭣�ֻҪû������ͣ�����������ж����ʮ���е��ݶ��ڷɱ���һ��ͣ����ֻ�ܱ������̤��
���������ǽ��˹�ͷ�����Ľ����������������������������Ļ������죬��ص�ǹ��ȴȫ�ǹپ������ģ�ֻ�йپ������װ��������率�Ѫ���̫������ʱ����Ұ�ϵIJ�ľ�Ѿ���ѪȾ���ˡ�
�ڶ�����ʮ���¡����Σ�3��
�����������õĶ����ڣ�Ѧ»��Ȼ�����ɵĿ����ڶ����ʣ����ŏ�����ӱ������ˣ����ڡ����Ǹ��ط��С������Ա��и�Ļ�����ѵ�����ʯ���塣��
�����Ⲣ������ΪѦ»���ְ�أ���������Լ��������λ�õģ�ֻ������פ�����ǵط�ʵ���Ǹ�̫ƽ����С�ط������˶�ûע�����֡���������ŏ��������Ӷ����ǧ������һҹ֮����ʯ�����������ر�����ɽ���������ǵط�������ԶҲ�����˵س����ڸ��õĹ�Ա���С�
������ǫ��һ���糿�ͷ·�ƣ�������࣬������ɫҲ�������е�ݻơ���ʱ�����������ܵIJ�����ս�ܵ���Ϣ�����Ե�����Ҳ����ʮ�����ܡ�ͻȻ��ʧ��һ����������ٸ������ȴһ������Ĭ���ԡ�
������ǫ��Ȼ���ָо����ط��Ͼ���һ̲��ˮһ����û��һ������������ڳ¾ɵĵ���ľ���ӡ��Լ�������ƽ�������ŵ��Ĺ��佫������������͵���һ�������һ����Ȼ��������ò�ƺ��гǸ������е������أ�����Ѵ����ҳ�һ˿�©����ƫƫ��������ʮ�ֵIJ�˳�֡�
���������۹��Ѿ�����������ʮ����ͷ�ˣ��ڴ�һͳ����ԭ���������Ȼ�����ᡣ����������ʱ�����������������ѳ��ֹ̻����ƣ������ϵĽ�������ⷿ����ļ������ӣ��������������Ǽ����ˣ�ż�����˱�Ⱥ���ż��Żỻ���µ���ס�
��������Ī���ĸ�������ǫҲ�о�����һ˿ƣ������롣�������Լ�Ҳ��������û������������Ȼ��������ʮ�꣬�����˱������˻���ƽ���ȣ�����һ�ɹ���������ͷ�����뻨�Ĺ���Ҳû�˸�С���������ȣ���������ͬ����·�ӣ��ƾ�ı�������ͳ�͢�س����ţ�ʱ�̹۲��Źٳ��ϵķ�������ʱ��һЩ��������Ѿ��м���û������ˡ�
��������һ�������ǫ���㽥�������ֵ���������лָ���������ʵ�ܼ��ڴ���������������ݵȷ���ǿ�ڳ��˵��˶�Ը�����٣�����·�����ܵõ��Ƹ�����������λ�������ȵȣ�����һ��������Ҫ�ġ�
��������������֮����û������Dz��Ǿ��������Ѿ��ˣ�����ǫ���ص��ʵ���
����Ѧ»��ü�����������ڣ���û�����������Բ�����ս���¼�Ϊ���������������˶�֪����ʹ�ò������ؽ�������ͨ���������Ƶо�֮��ΪҪ���²�˫����ս����ɱ�˵з�������ʹ����������������ɥʧʿ����ɢ��������ɱ�������Ѿ�������Ϭ�������Դ����ٲ��ڿɴ����ף�˫�����ݣ�������δ�ӵо���ʵ���·磬���ս��ʵ��ȡʤ����
������ǫ��ͷ��ͬ�����䲻���佫����Ҳ����õ�ս���ϵ�����������Ѿ������ٲ�����������Ӧ��Ҳ�ǿ��ŵġ�����Ѧ»��������ʵս֤ʵ�ˣ������������յ���ϢҲ����ˡ�
�����������������˿�ʼ��һЩ���ӣ�����˵Ӧ�ð������������¡�����ȳ��ڣ����й������й��أ������ɳ����������Ԯ������û���˸������ظ���֤�ڼ�ʮ�Ŵ��ڵĹ����£��Ƿ��ܼ�ֵ�Ԯ�����������ҳ�ɳ�ֲ����ڳ��Ĺٽ��ǹܵĵ��̣�Ҳ����֤�����Ƿ��ܼ�ʱ��Ԯ�����˸��ѱ�֤һ���ܻ����Ѿ���
�������ʱ����ս����Ա�ٶȺ������ر���ũ�����ҡ������Ϻ���һʡ���ܼ���ʮ���ģ�ľ��ӣ�����ƽʱ�κ��������Ա�����ô���ģ�����������Ƿ�ɢ�ڸ����������������������У�Ҫ�ۼ�������ɴ��������Ҫһ����ʱ�䡣��Ѳ����������������ɣ�����Ҳû�취�ڼ���֮�ھͰ�һ֧����Ū����������Ԯ������Ҫ���ӵ�����ƻ����ĵо���
�����������ϲ��ϳ�ı���ߣ���������ʯ����һս���Ѿ����Ӷ��ӡ�
������������ɢ��������������������������ʱ����ͨ��������η��������Ҳ�������в����ˡ���ǫ���뿪����ȥ��Ѳ���йݵ�·���������ء�
������˽�¶����е�����˵������������Ӧ�������֮���ٺ��Ѿ���ս������ʱ���в����졣���¸���һ��ཫʿ�Ǻ�������������������û�б�Ҫ����������ط�����
��������æȰ������ѧ���۳��µĹٽ���δʧս�ģ����Dz�����ս�ͳ��ˣ��������������ùپ�����һ������������پ�֮������˵��ȥҲ��̫��������
������������ǫ��ǰ�Գ�ѧ����ʵ���������ҵ������ֻ��һ���������Ե�ʡ�
������ǫ�����������ⷬ���ĺ��ĵģ������������ʧ�پ��������棬ʵ����Ϊ��ǫ���ǡ���������ʧ�ؾ���Ī����������ͨ����ǫ���������һ�����������ﱾ���ж��һ�����ؾ������������ڳ�͢�ٳ���ʵ�ڲ��ý����������������������س�ս�ܵĺã�����һ��û��ס���ӵijdz�Ӧ�ø����ε��˾Ͷ��ˡ�
����û��ס�ǣ�Ѳ����Ϊ����һʡ����Ҫ��Ĵ�����ȻҲ����һ�������Σ������ܾ�����ܱ���Ѧ»Ҳ�Ѳ��˸�ϵ�����������˾����Ҳ���Է�ٺ�ͽ䣻���г��¸���֪������Ϊһ��������ס�Լ���Ͻ��������ְ��������̡����������Ѳ���ĺڣ���ȫ�����Ҹ���������������⣬�����ڳ������û��ɽ����֪����
������ǫ�ݻ��йݺ���Ժ�����һ��ʯͷ���������ã���ʱ����˼��ʱ��̧ͷ̾Ϣ������һֱ������վ�������Աߣ��粽���롣
����ū������һ�����������ϸ���DZ��DZ����и�ȱ�������и�Ѿͷ��С�İѲ豭������һ�£���ʱæ��˵Ҫ���µ���������ǫ˵����Ӱ��ʹ�ã���Ѿͷ�����ˡ�
��������֮����ǫ�����ض�����˵��������ȥ�����������˵���ҵ�����������������ƶ��پ��������µķ��ԡ���
�����������㶣���֪��ʦ�Ѿ��¶��˾��ģ�ȴ��Ȼ�̲�ס�ٴ����ѵ��������Ҫ��ô����ô������Ѧ���˵ȶ���Ҫ��ӡ����ʽ���ġ���
������ǫ����������գ�����˵������˭��֪����������õķ��Ӿ������ҳ��ˣ�Ϊ���Χ��ʱ����ס��һ���ս����ʵ������������ν���������������������Ҫ��������Σ���ij����������λ��ǵ�����ġ�������������Ҫ�������DZ����ű���˵�գ��ҵ���������������
����������������һ�ϣ����������˵����ѧ����������
�����ܿ�Ѧ»��֪����������������ʤ��᷵ȶ������йݼ���ǫ�ˣ��������緹���˲��ϳԡ�������������䶼����ɵ�ӣ����������Ƶģ�֪����ǫ��������Ϊ���DZ��ڹ���
�������Ķ����ⳤ�ģ���ǫʵʵ���ڵص�ǹ��һЩ�佫�Ļ��м���������Ϊǰ�����ʾ���һ���Թۺ�Ч������ǫ�����Ѷ��������˵���˵������������Ϊ����Ѳ�������Dz����dz���һ�ء�����ֵ����֮�Ϊ���߲�ֻ����֮�Ѿ���Ѳ���������а��ţ���λ����ֻ�����������ǡ���
��������ֻ����ǫ�������ޱ��飬�����������������һ�����˼�״������룬�²��Dz�������ܵ���������в�ˣ����Ժ������Ҫ��������ʵ��֮��ġ�
������������£���ǫ�ּ���������ˬ��ش�Ӧ��ı������������¸���
�����������Ǹոճ���������������ˣ���Ѧ»�ݵ��������ź�ү�ȸ��ߣ���ʦ��˵�˼��仰�����¾���Ӧ��˵����ү������Ѧ»��������������˵����
��������ʦ�ԣ����ɷ��ߣ��������졣���䶮�÷��������٣�֪���˵��˸��١����������
����Ѧ»����������ĥ��仰ʱ�������ֵ�����Ѳ����Ը���ý�ʿ����ν��������������λ����֪�ܶ����£����պ����ڽ���һѩǰ�ܰ�����
����Ѧ»���ն�ʱ������Ȼ�����й���������һ�ۣ����Ŵ��Ź����ذ���һ�ݡ��������ٽ���Ҫ���ŵö࣬��֪����Ȼ�����̨����ʹ��ʧ�������ʵ������ڴ���������ʯ�������������¹�ֻ�����������˼ҵ�������һ��ͯ��ϰ������֮��һ���ڴ��˲���������Ϊ����֮���ʣ�����ͬ����������ĸ������
���������������ſĿ���������֪�����𣬺��ۼ��������µ��²����ܿ������ף����ļ���һ���dz������������ĸм�����һ��Ҳ��ʵ���������ǫ�����˾��⡣
��������˵Ҫ֪������٣���Ǯ���һ�ԣ����ڹٳ��ϣ����������Ӽ�Ч�������ܺ���֮���ܡ��������ò�����
�������ú�Ѧ»Ҳ�ھ��з���ѵ�⣺�Ӹ߶������ݣ��ٵ����£��پ�һ���ٰܣ�ֻ�����֮ս��Сʤһ�������������佫���������Σ�������ܽ�������ƽ���ط����ڳ��������˶�Ӧ���������������Ǻ����ܵ���ж���Ρ�
�ڶ�����ʮ���¡����Σ�4��
���������úܿ죬������ʱ��������Ƽ��ġ�ǧ��ѩ�����Դ���һȦ�������������ı��ϣ��������ͷ��������ֺ�����������ʮ�����䡣����̧ͷ����ս���������ưܳ�¥��һ��ʿ���Ѿ��ѻƵ���ȸ����ϳ�ͷ��
����������������·�ߵĹ������Ѿ�����ɥ����ϥ�����������۶�û������һ�ۡ����¸��������Ա�Ѿ����ˣ�����Ȼʣ���������������Щ����ǵ��صĵ�ͷ�ߣ����Ǽ���Ʋ����ڳ��£�ƽʱ�ڰ���ͷ��������������ֱ�����ջ���Ȩ�����ˡ�
����Ƥ�ĵ��û����У�һ�Ӷ���ȸ����ʿ����������ʽ���ν��볣�¸��ǡ���������Ь����ؼ�̤�ڵ����ϣ������������ĵ������Ų������������ֳ��������е��������ͷ·���ʾ���������ͽ�����Դ������ȵ��ѿ��ٵ�Ͷ���������������������Ҳ��Ͷ���ġ������ؿ��ܲ�̫ӵ�����Ѿ����Ľ�ռ��������Ҳ����Ϊ�ⳡ��ս������ν�������������ڡ�
�������dz������dz��£�Ҳֻ����ǫ����ô����������ع����Ҹ�̾��һ����
��������漴����Ц��������������һЩ���⣬Ҳֻ��ʤ���߲����ʸ�������Ц���ˡ��������Ǵ�������������˼�ˣ�������û�г�Ц��ǫ����˼��
������������ʷ������ǫ�ڱ�������ս�еı��֣���ʱ��Ӫ��ʮ����ɥ���������������ڱ��۵������С�������������Ǩ��������ǫ��Ϊ����ս��������Σ�ѣ��������ȴ��ô���ͷ�����ȴ����ʵ������ӡ���в�̫������������������Ե�˼ά���ս�������ĽǶ���ǫ��ô����������õ�ѡ����ȸ���Ļ��������Ѿ����������ʱ���ľ��·�չ���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