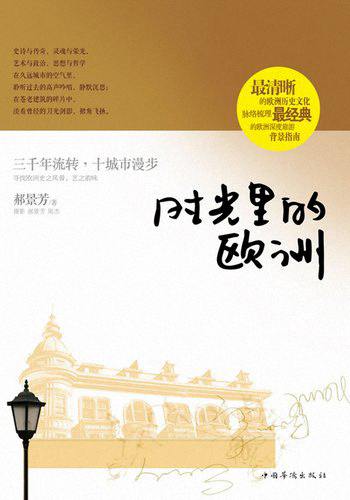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我逼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让自己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姑娘们笑声朗朗,同龄的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却独自一人枯坐桌前,像是铁匠打铁一样,使足了劲,写下一个又一个硬邦邦的汉字。后来,经常会有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汇,就是「写作」。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我十分怀念一九八〇年代的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一些被禁止了十年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还有更多新的文学杂志正在涌现出来。一个几乎没有文学杂志的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种文学杂志的中国。于是大量的文学版面都像是饥饿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时候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无论是出名的和还没有出名的,他们所写下的全部作品,仍然无法填满如此众多的文学版面。因此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
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杂志社对「邮资总付」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读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镇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不准你打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掮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证明?」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
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