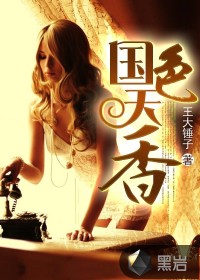天香-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牍矗噶耸鬃郎系男旃馄簦嚎醇唬磕遣还桓鲂悴牛从胂认推狡鹌阶炯啤矗坎皇枪γ侨瞬牛∩倌昝嵌纪亲揽矗匆皇被赝匪担核滥兀克挡欢ńT谙恢校环ⅲ只蚋纱嗑褪歉龃啦牛』白叫旃馄羯砩希陀腥怂担禾舜旒移逗臼侵痔铮缓蟮缴虾3抢铮鲂┱胪废吣缘穆蚵簦卑桶偷毓┝硕恋闶椋俣嘁膊荒芰耍懈鲂悴攀凳舨灰祝阅痰木⒍际股狭恕S钟腥怂担壕鸵蛭移叮坏靡讶ネ庀缱鲔邮故悄挥眩棺吡诵┑胤剑耸烂妗=幼啪陀腥饲懒怂担核源硬恢朗裁吹爻〈镏掷椿ι稀裁次镏郑咳嗣俏省D侨舜鸬溃焊适怼R惶饬阶郑篮湫ζ鹄矗杭炔皇恰爸侄埂保膊皇恰安删铡保我猿隼匆桓觥案适怼保空馐保P说话了:大家莫笑,英雄不论出身,太祖还卖过白薯。众人更笑,煞也煞不住,终于笑停了,阿昉接着说:沪上这块滩地,蛮荒得很,却藏龙卧虎,不说远,就说近,赵兄家的那伙计——众人又笑了一拨,怎么连伙计都出来了!引得那几桌都转头看,不晓得笑的是什么,只以为少不更事。阿叻却坚持要说赵伙计,这一回,赵同学也符合了,人们才静下来,听他们说。只有阿奎不自在了,因这赵伙计牵连着他那一档子事,生怕会说出来。本来他在这一桌上就有些窘,高出一辈,又不出息,这时更坐不住了。趁人们都听阿叻说话,起身离席,去女眷那一桌,找他母亲和媳妇去了。不料,这桌上已有一个男客,也是来自他那一桌,就是阿潜。
阿潜挤在大伯母和希昭之间,转过来喝大伯母杯里的酒,掉过去吃媳妇箸上的菜。要换作别人,就会招耻笑了,可这是阿潜呀!从小得到大伯母宠爱,一是不敢笑他,二是见怪不怪,由他如何粘缠都无人可说。阿潜喝着吃着,絮叨着将那几桌上的话拣中听的传过来。多是夸天香园里的绣品,称天下第一针。小绸不免得意,说别家针线不过是闺阁中的针指,天香园绣可是以针线比笔墨,其实,与书画同为一理。一是笔锋,一是针尖,说到究竟,就是一个“描”字。笔以墨描,针以线描,有过之而无有不及。小绸这话既是说给众人听,更是说给希昭听,知道她一心只在书画上,又将书画看得比绣高,骨子里是男儿的心气。小绸自己电是男儿的心气,所以越加不服希昭。这婆媳俩犯顶,多少是像江湖上有本事的好汉,谁也不让谁。
说到绣,桌上人都有要说的。阿昉媳妇道:娘家时,从小就听说申家有绣阁,母亲常与父亲说,咱家的园子虽然气派,可天香园有出品,就好比山不在高,在有名寺。二太太说:天香园的绣,追根溯源,是从闵姨娘起始的。闵姨娘说:这绣已不是那绣,原先不过绣些衣裙鞋帽,来这里以后,才绣大件,帐幔屏罩,无奈从仅有的针法里,逼出许多变法,所以早和苏州娘家的绣活不相干了!人都以为闵姨娘说的是谦词,但至少有一半实情,一桩桩细论,果然,滚针是从接针里套出来,旋针又从滚针里套出来;再派生出套针、集套、单套;掺针里套出施针,施针里套出施毛针……可谓针针相连,环环相扣。正说得热火,阿奎忽然发声:嘉靖年大理寺评事,本邑顾砚山,家中就有绣女如云,其中有名叫萍娘者,曾绣成一幅“西村赛社图”,人物牲畜,栩栩如生,顶有趣的是一名村妇,携一个乳臭未干小儿,正解开裙带上荷包,取出一枚钱买炸果子,小儿垂涎的样子十分好笑。方才说得兴致勃勃的人们,犹好像被泼一盆凉水,顿时无言,静下来。略停一时,小绸冷脸问道:你见了吗?阿奎不由嗫嚅起来:虽没亲眼见,却听亲眼见的人说来着!阿昉媳妇说了句:叔叔认识人多,也许真有亲眼见的人!小绸冷笑:你叔叔就是认识人多!阿奎的娘和媳妇面有羞色,都低下头去,阿奎自己也觉不自在,起身回原先那桌去了。
25 武陵绣史
晚上,希昭对阿潜说:大伯母也忒厉害了,当了人家亲娘媳妇,还有小辈的面抢白叔叔,让叔叔一家都下不来台!阿潜就说:叔叔向来就会扫兴,别人只是不说,不像大伯母一口气说出来了!希昭说:你总是护你大伯母!阿潜伏在希昭耳畔笑着:我心里最护你,可是不好意思。希昭推他不开,只得任他缠绵一回。阿潜看她若有所思,便问出什么神呢?希昭说:叔叔所说的“西村赛社图”,或真有其事,隐约中,仿佛吴先生也说过有一种绣画,早在北宋,开封都里遍传汴绣,宫里也设绣阁,曾绣过一整幅长卷,“清明上河图”,后来遗失在南迁途中,要是能看一眼都好!阿潜不以为然:后朝想前朝,不晓得有多少繁荣胜景,是怀古心所致,事实上未必,只怕大不如今。希昭反诘:你又怎么知道,难道你有过亲历?阿潜说:读书啊!书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可见古时蛮荒。希昭说:上古时候,一团混沌,后经三皇五帝夏商周,十二诸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秦王汉武,到唐宋已是一片新天地。阿潜说:为什么挡不住蒙古人?那食腥膻的人种,和上古时候只怕差不多,倒将一个盛世王朝夷为平地!希昭驳道:这就是盛极则衰,如月满则亏。怪不得人事,而为天道。阿潜有些说不过,耍赖了:你崇古你却回不去,我崇今恰恰生在现时,还是我便宜!希昭翻个身,不与他理论,阿潜兴致倒上来了,十分得意:我就觉得现时最好,真可谓圣人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人间之大德!据说你们杭城有一道菜,是将极嫩的肉切成极细的丝,再穿进绿豆芽中,咱家还没有试过。希昭嗤道:这不是吃,是折腾人,刁钻古怪,还“圣人之德”呢!阿潜说,你不是崇古吗?古人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古人所说难道也不屑?希昭再不说话,以为她睡着了,凑过去细看,却见睁着眼。再要叫她,一闭眼,睡了。
以后的几日,希昭对阿潜都淡淡的,以为是那晚说话不合,生气了。但也不顶像,起居都正常,只是不大跟阿潜玩了。要说跟阿潜有什么玩的?不外是读书写字作画。如今呢,还是读书写字作画,却是一个人,拉上幔子,事先多了一道洗手,再又焚上一支香。有几次,阿潜进到幔子里,与希昭说话,见她神情肃然,有一种虔敬,便又退出了。阿潜心里不安,恍惚中,这情景似曾相识。在他极幼小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是焚香洗手,凝神端坐,渐渐地就离开了他们,那就是父亲。四季祭祖,阖家一并进到莲庵,庵中主持,一个青衣披发人,添油点烛燃香,默然无语。每当祭祀完毕,便在祖父祖母跟前俯地叩首,又向大伯父大伯母作长揖。阿昉阿潜从小怕他,离他远远的,觉着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阿畴的乳母告诉他们,这就是父亲,就更可畏了,因为知道与自己有关联,就要牵自己去那虚无之中。平时在园子里玩耍,他们从不走近庵子。庵子后面的白莲泾,已让柳林遮得婆婆娑娑,照理是美景,他们却感到森然,而且戚然。他想起希昭曾和他说过的,出生那月的朔日早晨,一个庙姑敲门问路。以杭城习俗,这日里第一个敲门人是女,婴儿便是女;是男,婴儿则是男,一个姑子,又是何兆呢?阿潜不觉郁闷起来。大伯母看出了些,问他哪里不妥?他摇头说没什么不妥。又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来来往往,希昭到哪里去了?回说在写字作画。小绸戏谑道:阿潜娶了个才女!阿潜不做声,小绸正奇怪,见侄儿已悄然而去。
三月里,城里遍传,一头白鹿,身高丈余,从吴淞江上游过来,穿芦苇荡登岸。大人孩子拥簇尾随十数里,只见越走越快,渐渐跟不上,终于绝迹。人都说是祥兆。回顾近三年内,天无灾,人无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城内城外喜气洋洋。四月初八,是为释迦牟尼诞日,龙华寺、大王庙、水仙宫、广福寺、静安寺,子夜时分便开寺敲钟,香烛齐燃。肇嘉浜、方浜、香花桥、穿心河,两岸都是活鱼活虾、龟鳖蛇蟹,专供放生用。又有马、牛、羊,鹏、鸭、鹅,是放于河滩旷地。一时间鸡飞狗跳,鱼乐虾跃,桥上桥下一片欢腾。其时,日涉园已呈大半轮廓,三十六景有二十四告成,尔雅堂、来鹤阁、明月亭、桃花洞、殿春轩,等等等等,规模不在愉园、天香园之下,从此并称沪上三大园。愉园的壮美,日涉园的雅丽,皆不动之景,惟有天香园绣千变万化,是园子的神韵。如今,又有一说,就是九尾龟。不免以讹传讹,说是园中池子里捞起来的东方神龟,对日吐火。虚虚实实,天香园声名大振,竟超过前期,桃林、墨厂、莲庵,遍地花开的全盛之时。因此,世人将其列为沪上三大园之首。
这一年,阿奎和阿昉各添一女,因天香园从绣阁得名,所以申家并不视弄瓦为轻,甚而更器重些,阖家上下都很欢喜。那蕙兰已交九岁,却与阿奎十二岁的长女采藻齐肩,形貌端肃,坐在花绷前,拈一枚针,上下穿行,不一时就有一朵小花呈出绫面上。其时,绣阁中足足三代人,第一代小绸、闵姨娘为首,勉强算上阿奎媳妇和落苏;第二代阿畴媳妇、采藻、偶回娘家的采萍、颉之、颃之;第三代即蕙兰。满满当当,绵绵延延,小绸却总觉得有一个空,少了一个人,就是希昭。
遭希昭冷淡的日子里,阿潜结交了一个朋友。正月初二宴请本邑名门贤达,造山大师张南阳携来陈进士家一名孙辈,陈俊再,坐在阿哜阿潜他们席上。俊再年少阿潜两岁,这年二十五,家有一妻二子,却还是少年模样,极为清秀,生性也十分天真,每每见申家女眷,不由地便面红耳赤。那日宴上,阿潜或是去与大伯母希昭纠缠,或就是与这位俊再说话。阿潜长年球在家中,人们又宠他,对外头的人和事其实是生畏的。而这陈俊再比阿潜更胆怯,不时地回头去望带他来的张大师,想过去又不敢,因那一席是比这一席更可畏的。由此,阿潜便负起照顾的义务,桌上的话题他本也插不进嘴,就专和俊再应酬。一席下来,两个腼腆的人便生出几点儿情义。数天之后,俊再遣人送给阿潜一封书信,素白纸背有蓝云隐花,极娟秀的小字写有三四行,是为感谢款待,又赞扬对方人品,甚感三生有幸,诸如此类。阿潜接信后,几近狂喜。二十七年来,惟有的交际即是年少时,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半年塾学,所谓同窗在阿潜看来,无一不是粗鄙与鲁莽,而今这一个好比天外来客,如此这般的风雅。赶紧铺纸研墨,要回信过去。落笔时在措辞问迟疑好几回,热情了怕狎呢,客套了怕生分,来去掂量,方才定在以本地人文比兴,称颂对方品德,“古今来地以传,槎里褊小,而尚论其人”开头,完全是一篇道学文章,王顾左右而言他,最终不知指向何处。不几日,又得俊再一纸信笺,吟的是上海河川地理,也是一篇论说。如此这般,两人越写越多,古往今来,天南海北,洋洋洒洒,穿梭似地互从往来。文章写毕,接着是诗词,一首对一首。还有画,一幅尺素,题一曲小令,盖一枚印,于是又得去找人刻印。大约二三个月以后,春暖花开时节,俊再发出一封请柬,减邀阿潜去“敝舍”喝茶面教。此一生,有谁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