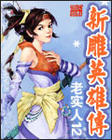清末英雄-第9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一入学部就看到章士钊,还有一个身着西装的斯文留学生。此人正是胡适,他和章士钊是通过陈仲甫刚刚认识。
“这,仲甫呢?”亲切的和胡适打过招呼后,蔡元培顿时询问陈仲甫。
“孑民啊,你们这政府比廷尉府管的还要严啊!”章士钊一来就抱怨道。“仲甫虽然留日数次,可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虽好学可就是没有拿到文凭。可他又不想参加吏部那个什么同等学力考试,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想来京了,打算去新加坡。”
“这怎么行?”政府的管理比原历史正规多了,办学的金额也多了几十倍。可正是因为政府管理正规,陈仲甫这个连中专学历都没有的海龟无法像原历史那般,在蔡元培的操作下顺利被北大聘用。同样的,十年后才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现在名头上还不能用博士二字。
胡适在这里不说,听闻陈仲甫要走,蔡元培顿时不放,他站起来道,“仲甫之才岂是学历文凭能证明的!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孑民。不急不急。仲甫还在我家里住着呢,还没走。”看见蔡元培着急,章士钊立马将他给拦住了。他其实就怕蔡元培是为了应付自己才答应招聘陈仲甫的,所以先过来谈个风声。“不过。他不想参加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同等学力考试,你就看怎么办吧?”
“我一会去银安殿……,”蔡元培本想去杨锐哪里走后门,可觉得这事情真是太小,求情成不成不说,万一让杨锐感觉不对。那事情就不好办了。脑子里想着陈仲甫学历的事情,蔡元培又看向胡适,关心道,“适之,来京城还习惯吧?”
“谢先生相询,此来京城……”胡适说道这,扶着眼镜笑了一笑,一言难尽的道:“还真是感觉不太习惯。”
京城从开国开始,就一直在修补新建,为此花去的钱海了去了。神武元年是内外城墙、皇宫,神武二年是各种防御工事,之后则是道路、下水道、行道树、西式草坪、路灯,公交站……;今年连承天门天街以及千步廊的围墙都在拆建,说是为了明年年初大阅兵——这是礼部和总政一般人绞尽脑子想出来的法子。整个京城长安街可阅兵,可长安街又有T字形且封闭的天街,这又是要保留的,所以只有将天街的砖头都编上号码,拆了全砌在在钢铁架子上,这种架子装有无数轮胎和大型船用发动机,需要时可发动机器移开,不需要时则开回原位,以再次形成T字天街。这么一搞,整个天街都变成活动城墙了,只是数公里的天街围墙这么一改,花的钱据说有好几百万。
胡适不像蔡元培这样知道细节,他一到正阳门火车站就觉得这城市非常非常的干净,城内建筑虽老旧,可西式国家该有的公共设施一样不少,而且,不少地方的细节做的很精致,特别是火车站的厕所,漂亮的让人都不敢进去解手。这种中式建筑城市,结合现代化设施,再加上精致舒服的内里,怎么看都要比粗犷的美式城市美得多,只是,这些感受他是不好讲。
“孑民先生,我已给自勋先生去电,学位的事情,自勋先生说他会帮我想办法的。”胡适的论文只是大修通过,而缺失博士头衔在国内吓不到人,所以只能拜托虞自勋了。
“那就好。”事情终于去了一件,就剩下陈仲甫的麻烦事了,蔡元培的心情终于好上了一些,觉得开学风之先又近了一步。
辛卷第五章无辞上
“学校的历史就不说了,之前是京师大学堂,开国后则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学校现有文、法、理、商、医、农、工七个学院、三十七个系,教授讲师所有的教务人员共有三百四十六人,在校生人数共计三千六百余人。
学校的管理部门分为校董会和教授评议会,校董会主要负责学校的行政日常事务,使师生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以专心任教及学校;教授评议会由各个学院推举的教授参加,主要是管理教学事务;除了校董会和教授评议会,学校还有学生会,这是学生所组成的半官方性质的机构,主要是管理学生社团和一些学生事务。
学校教学采取学分制,即将课程分为基础、专业、选修、必修四种,每一种类别的课程都有相应的学分,各个系的学生修满各种课程所需要的学分后,即可毕业,未必要四年才能毕业。不过相对的,因为各种课程都由学生自选,所以老师的薪资除了和等级有关外,还与选修人数的多寡息息相关,而学生选修人数的多寡则在于老师的教学水平——不同的老师开相同的课程,水平高的自然听的学生就多,学校里有阶梯教室,可坐两百人,如果老师的教学不被学生认可,那么听的人就会很少……”
几经周折,终于将入职事务办妥之后,蔡元培的秘书徐宝璜便越俎代庖,开始对胡适和陈仲甫两人坐最为精简的入职培训,只是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对大学的入职培训并不完全清楚,基本是想到什么说到什么,从选课岔出来薪资后,他又顺势道:
“大学教员的等级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种,其薪资是我国各行各业中最高的,适之先生现在是副教授,基本月薪为一百华元,若算上讲课津贴。应该不会少于两百华元。这只是私人所得部分,另外教员还有学术资金,这种钱会因所属学校、院系、等级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北大是重点学府、文学院又是全国重点院系。教授每年所申请的学术资金没有两万也有一万,这主要是看学术研究的价值;
而资金的申请对象可以是本学校,也可是学科所属的全国学科委员会、稽疑院的教育委员会、皇家科学院,甚至若是实用项目,还可与校外公司合作以获取资金。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太多太繁琐。我在此就不多说,正式上班后学校会下发教员手册,上面会有详细介绍。
孑民先生说仲甫先生的职位为文科学长,其正式的名称应是文学院院长,属于行政系统而非教学系统,另外文院长现任院长是夏锡祺先生,只是他同时又兼任教授,所以仲甫先生到任后,他会将学院事务移交给仲甫先生好安心教书。
我国官员的薪俸一向是基层官员略高,中高阶官员较低。与日本总理内阁大臣相比,总理的薪俸只有日本总理内阁大臣的七分之一,为一百三十五华元,这还要交个人所得税。仲甫先生虽为文学院院长,但也是参照政府薪资给薪的,院长一职的月薪与正四品官员以及军长少将的薪俸持平,废两该元之前为三十四两,换算成华元则是四十六块五角七分五厘……”
胡适这边若算上学术资金,一个月有一两千之巨,而陈仲甫虽是文院院长。可工资连五十块都不到。徐宝璜有些歉意的看了他一眼,想接着安慰,不想陈仲甫却问道:“这个薪资也要交个人所得税吗?要交的话应交多少?”
“各省个税起征点都不同,京城是月入七元以上者要交个人所得税。只是从七元到十元税率都很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十元以上才渐高,四品官的的税率大概在……,大概在百分之十二上下。”
以时下的银两购买力算,一两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在杨锐看来约等于后世的一千,理由是北洋新军四两二钱的月饷就能养活大城市里的一家五口并还有少部分结余。而之所以用粮价去折合不恰当,在于现在的一般人家除了吃饭并无其他消费,而后世商品泛滥,粮食的消费比例极小。因此,个税在全国都是从四两开始起征,八两开始暴涨,四品官的月薪三十四两,即为后世三万四千人民币,按后世的个税税率,税率应该是百分之十八,不过,单纯从从消费折合币值,这又不尽合理。
如按一两等于一千人民币算:三两一石的大米在后世应该是三千块,合二十多块一斤,贵了近十倍;八分钱一斤的猪肉在后世则是五十块一斤,贵了两三倍;两毛钱一场的电影放在后世就是一百五十块,贵了近两倍;二毛钱一份的茶点,放在后世就是一百五十块,贵了近两倍;房租大四合院一般每月需六两到十两,中等单间二两上下,放在后世……似乎持平;
火车从北京到天津二等座二元三角,是后世的二十多倍;市内黄包车五分起、公交两分起,为后世的三倍和十倍,以后黄包车改出租车后,就不知道是几分了;馆子里请客,普通的四冷四热四大碗最后再加一大件,一桌一两银,比后世略贵,高级酒店的鱼翅席,加酒水小费需十两,比后世贵;住家自己做饭吃,小康水准每月需五两,是后世的三四倍;另外还需再请一个专职下人月薪二两,比后世略低。
再说青楼,上等的开盘子就要两元、过夜六元,杂七杂八打点不算;中等的打茶围京钱五吊,合华元六角,若是要开铺留宿,京钱十吊,合一元二角,小费也不在其内;下等的就不必提了,只有中等的一半。
陈仲甫一家好几口,真要住到京城来,那每月光住和吃就要十六七两,虽有结余可看戏喝茶置衣,可要进行高级一些的消费便不可能了。最少高级妓院去不了,那里的规矩是不开个三五次盘子,姑娘的手怕是碰不到的,留宿更不待言,即便勉强去了,也将处处显寒酸;而去中等的窑子打茶围。不说那里的姑娘不会唱歌弹曲,就是会,院长大人也丢不起这个脸啊。当然陈仲甫考虑的根本不是能不能逛窑子的事情,他只是觉得这教员和官员工资相差太大了。这还要交税,这么一下六七元又没了,以个人收入计,真不如找个大学做老师算了。
徐宝璜不知道陈仲甫的心思,只是讲一些学校的福利。“仲甫先生,京城地产大部分都被户部买下,官员住宿都有房贴,要求不高的话自己并不需出多少钱;而学校是免伙食费的,虽只限本人,但也能省一些钱;再则是汽车,官员、教员,按照相应的等级将会配发公务车,虽现在汽车还在试产,但欧战结束后。工厂空闲下来便能生产,这个时间最多只要五年。”
“正如孑民先生所说,我们是开风气之先来的,不是挣钱来的,薪资只要生计不愁就行,这些都是枝节。”看出徐宝璜的担心,陈仲甫只好勉强笑道。
“那就好!”徐宝璜见他笑也就放心了,其实以他刚入职从八品月薪十块出头的薪金看,四十六块已经很多了。
“还是说文学院吧,现在一共分了四个系。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英语。教授中旧教员甚多,其中陈介石、陈云从、黄季刚、辜汤生、马彝初、林琴南、黄玉昆、刘容季等人名望最盛,学术则是陈介石、刘蓉季、黄季刚三人最高。陈介石先生年已老,估计教不了多少年了;
刘蓉季是刘申叔之弟。扬州人士,刘申叔与复兴会有些旧怨,但开国后在章枚叔的求情下,这些都不但不再追究,还将其弟招至北大当教授,其家治左传千年。学渊源深厚,众人皆服;黄季刚则是湖北蕲春人,曾留日,入复兴会,来京和章枚叔结识后形同师徒,他本是只想做学问的,但后来被学校请来,其人孤傲狂狷,目中无人……”
“这人我认识。”胡适不知道这人是谁,但陈仲甫却是知道的。某一次在日本,他在钱玄同寓所说起清末汉学,感叹大师戴、段、王等人都是江苏或安徽人,唯独湖北不见大学者。刚好来此做客的黄侃马上进门道:‘湖北是没什么学者,然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未必就是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