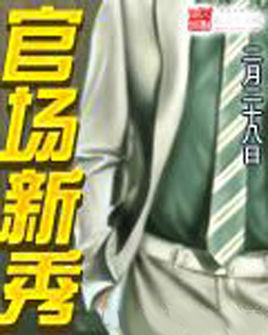首席外交官-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慈安太后摆弄着自己的指甲套,觉得这个话题似乎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她倒是要看看,这位年纪轻轻的沈大人,究竟要怎么把这黑的说成白的。
慈安太后露出了一个饶有兴致的笑意:“哀家早就听别人说起过,沈卿家的特立独行,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颇有点儿魏晋之人的风范,今日可算是开了眼了,不过沈卿家之言,哀家还真是想不明白,嫪毐一个**宫闱,谋反犯上的乱臣贼子在沈卿家的眼里竟然成了个大功臣了。”
“所谓功臣,是建立功绩之人,无论是敌是友,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提供了好处,那都叫做‘功臣’,母后皇太后娘娘不妨想想,秦末汉初之际,如果没有秦二世,没有楚霸王项羽,那汉高祖刘邦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朝不保夕的泗水亭长,萧何、樊哙之流也就不可能被载入史册。东汉末年,如果没有董卓入洛阳,祸乱京畿,十八路诸侯群雄并起,也不会有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机会,刘备、张飞之流怕是真得当一辈子的织席贩履,杀猪屠狗之徒,隋末炀帝之时,如果没有隋炀帝的暴政就不会有那场风起云涌的隋末纷乱,唐太宗充其量也只是陇西一介贵胄公子,毫无作为可言。胡亥、项羽、董卓固然是刘邦、曹操之流的敌人,但反过来说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敌人给他们提供了名垂千古的机会,胡亥、项羽、董卓、杨广,不但是这些人的‘功臣’说是‘恩人’可能也不为过。乱臣贼子又何妨?要不是这些乱臣贼子,哪有那么多千古明君得以为后人所传扬的丰功伟业,况且臣以为嫪毐为秦始皇所建立的功勋,可远远不止如此。”
年轻人的语气也很轻松,像是在开玩笑一样,但是无论是慈安太后还是这个年轻的官员甚至是一旁如同是塑雕像呆立着的老太监怀德也明白,这样身份的两个人在一起,哪怕是一声看似是毫无意义的浅笑也不能被当成玩笑,他们此时此刻任何一个动作都关乎着这两个人的未来,甚至是天下民命,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慈安太后也不能掉以轻心。
年轻人解释道:
“嫪毐其人。猥琐至极。**秦宫,谋反叛乱固然都是事实。暂且不论世人论及此事,将一切罪责皆归于假太监嫪毐和赵姬,并没有影响到秦始皇甚至是秦庄襄王的名声。母后皇太后娘娘只需设想一下,若果没有嫪毐,秦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年轻人顿了顿,又说:
“微臣以为,若是嫪毐不出现,那么赵太后和吕不韦的同盟就不会破裂,秦始皇就算是再雄才大略也难以撼动吕氏一门在秦国的地位。吕不韦门下虽有门客三千,不乏才俊,但皆为相国之命是从,赵太后权盛且亦用来感念吕不韦之恩,连六国使臣也只知有相国而不只有秦王。是时秦国必然是姓吕而非姓赢。微臣以为,正是因为有嫪毐的出现,才得让赵太后和吕不韦分道扬镳,也正是因为有嫪毐的出现,在秦国的朝野,才能出现一股可以遏制住吕氏的势力。而此两虎相争,自然无暇是时关注着秦王,才有秦始皇韬光养晦,重掌秦国大权的机会。”
慈安太后的眉头皱了起来,沉默了半晌才道:“沈卿家无需跪着回话,平身。赐坐。”
年轻人口头谢恩,又重新坐回刚才的位子,仍然是一副宠辱不惊的表情。
年轻人见慈安太后有所动摇,继续趁热打铁:“那年嫪毐祸乱大郑宫,尚未惩戒之时就已经在咸阳城内传得满城风雨,微臣以为,以秦王之英明,以其客卿李斯之睿智,乃至秦室宗亲必然都有所察觉,因此嫪毐后来造反作乱之时才会须臾之间就为昌平君所剿,但之所以会忍一时之忿,怕多半就是为了可以借嫪毐之手排除吕氏,也正是因此,嫪毐之乱没多久,吕不韦才被削官出京,最终饮鸠而亡。微臣以为,如今我大清官员包括皇上都不逊于当年秦国文武乃至于始皇帝,之所以三缄其口,其中深意,想必母后皇太后娘娘是明白的。”
慈安太后一愣。
她突然觉得此时的气氛有些奇怪,这个本来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左右手的年轻人,怎么现在反倒成了她慈安太后的智囊,在这里帮她出谋划策,而谋划的对象正是这个年轻人甚至是这个年轻人父辈的主子——西太后慈禧。
而且虽然刚刚这个年轻人为西太后慈禧算是好话说尽,但是其目的现在再想想似乎并不是在维护自己的主子,而是不让他沈哲自己趟进这趟浑水,说到底都是在为他自己打算,而再仔细想想他这一年的所作所为,虽然看似都是在为西太后慈禧服务,但是就长远角度来看,没有一样是对慈禧有好处的,至少没有一样是在加大慈禧的权力,反之更像是在不动声色地将西太后慈禧的权力一点点转移,甚至连他自己出身的湘淮集团,也被他比喻成了“吕不韦”只不过,当年的吕不韦与赵太后是相符相依,而如今的湘淮党则是依靠着慈禧太后。
慈安太后陡然糊涂了,搞不清楚这个从入士之初就被朝野上下定义为“后党”的年轻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不过,如果这么看来,最后的受益者似乎只有同治皇帝载淳一人而已。
慈安太后猛地一惊,觉得自己似乎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从来都不属于哪一边,他服从的只是当朝的圣上,也是代表着大清帝国的载淳,又或者,连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的载淳都不具备这个资格,这个年轻人服从的仅仅是自己的心智,而对与圣母皇太后的服从只不过正好是他全部谋划中的一个部分罢了。
这个年轻的世家公子,想要成为的根本不是霍去病那样的少年英雄,他想要像秦相李斯那样位极人臣之人。
所以,“赵太后”是他的障碍,而他曾经一度归附的“吕不韦”也是他的障碍,与“赵太后”一样,留不得。
第三十八章
8
沈哲到山东的时候,他才是第一次深切的感觉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个好官,至少当一个让百姓爱戴的好官,实在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上千年的愚民政策下来,不管是民风多彪悍的地方,只要上面还给一条活路,那么他们不管有清贫也会本本分分的生活下去,如果朝廷又大发慈悲地给了一点好处的时候,那他们祖祖辈辈都会感念这一点恩德。
正如很多年后的林语堂所言,中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明明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却偏偏具有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沈哲看到渤海边上,那些挤上前往辽东半岛的帆船,灰头土脸却还不忘为自己“英明”的君主歌功颂德,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在自己没有来到这个时空之前,还是江南一个大都市里的普通学生的时候,他的一位对历史颇有些建树的同窗曾经这样感叹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著名暴君查理一世生不逢地——“其实查理一世也没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不过就是关闭了议会而已,资产阶级的那帮人就是难伺候,这样的皇帝要是在中国,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明君呀。”
沈哲当时就觉得,如果一介政府,可以让这个世界时除了北朝鲜之外(当然这是在21世纪那个时候)最为高层考虑,最体谅政府,以及对于最高领导阶层通常抱有美好的幻想以及感恩之情怀的群体,忍无可忍以至于揭竿而起,那么这样一个政府肯定已经是到了它生涯真正意义上的终点,而且若是不作出调整,想在任何一个国家生存下去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美国纽约曾经形容他们的城市为“Youcandoithere;youcandoiteverywhere。”而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他的上层阶级的形容则可以是“youcannotdoitthere;youcannotdoitanywhere。”
而在山东,他是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愚民政策的力量。毕竟在沈哲以前的那个时代,不管怎么说还是信息发达,什么思想理念都接触得到,受西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各种传媒总会有一些愤青式的任务看什么政策不顺眼。但在晚清这样一个时代中,这一批人似乎并不存在,就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已经忘记了,当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的时候,朝廷是怎样地弃他们于不顾,避走热河,苟且偷生。
这些来自华北各省准备到东北的广阔天地里谋求生路的流民们也早已忘记了让他们丢失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山海关以外的蛮荒之地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他们现在记住的,只有朝廷体谅民情,放他们这些没钱没田的农民们一条生路,开了渤海的海禁,让他们去土地广阔的东北讨生活,将以前的每天通航一次,改成了每年就此,基本上除了天寒地冻的那两三个月,可以保证每月通航一次。
沈哲是三月初的时候接到诏书,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辽宁两处督办渤海海禁新政,接到诏书之初,沈哲还在考虑自己究竟去还是不去,要是不去,难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年纪不大,架子倒是挺大,保不准又让那些清流派抓住了他的这个把柄,大书特书,什么年轻气盛,什么难堪大任之类的,又都会毫不客气地往他身上招呼,而这种辞不赴命的事情他的义父李鸿章和湘淮军中的很多人也干过很多次,或是因为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或者是为了湘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过到了沈哲这个时候倒是没有了这方面的担心,而如果他再这么一效仿,那不是让朝廷觉得你们湘淮系的这些官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朝廷把你们伺候得太舒服了还是怎么地,这“抗旨不尊还”倒成了保留节目了。
但是沈哲不想去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他的初步设想现在已经悉数完成,而要是保险起见的话,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留在京城里多观察一阵子,而另外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一件事是此时已经到了同治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且不说按照正史来说年轻的同治皇帝载淳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就会患上“不治之症”,然后熬到下一年的年初就会撒手人寰,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日本会在不久的未来对台湾发起进攻,投石问路来打探清廷的态度,虽然这一年的战事是以日本战败而告终的,但是之后签订的《北京专条》可是一点儿都没让小鬼子亏着,反而还让前来谈判的伊藤博文从战败中找回了点儿自信。
可以说在沈哲所知道的那段历史中,就是因为近代中在于日本的交涉中这第一步走的不怎样才有了后来那么多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北京专条》的直接原因在一百多年后都没有解决,沈哲可不准备在重蹈覆辙。
就在沈哲左右权衡之间,同治皇帝载淳不是时机地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此次督察渤海海禁新策的任务,竟然是自他步入仕途以来就一直和他互看不顺眼,水火不相容的清流派的中流砥柱荀同庆。
沈哲起初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渤海这趟自己无论如何肯定是不能去,虽然不知道荀老夫子此举究竟意欲何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荀同庆所代表的清流派毋庸置疑是他这个洋务派的敌人。在对手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他虽然没有办法制定出一套详细的对应计划,不过还是可以坚持一个原则——敌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一定不要让它发生总是错不了的。
但是随后,有沈哲一手策划从清陵卫中分离出来的情报部门就可他带来清流派各位重要大臣的最新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