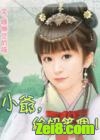一品驸马爷-第1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批的反应这么热烈,奖励这么丰厚,第二批开始时根本不需要谢则安再找托儿,群众纷纷捋起袖子加入到这次“文坛盛事”里面……
这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国为民啊,文章一出来,经费马上就位,乡亲们看向自己的眼神多么崇拜!多么敬佩!即使没选上也不要紧,听说这事儿今上、姚相还有少年成名的谢三郎都会经手,借机混个眼熟也好啊!啊不对,这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特别特别崇高,特别特别无私!
谢则安轻松自在地和谢望博品茶煮酒。
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戴石忽然行色匆匆地赶过来:“官人,有几批难民陆续往京城过来了。”
谢则安皱了皱眉,站起来说:“到书房细说。”
谢望博也快步跟上。
戴石掌握着驿站和报邸,第一时间了解到难民的情况。难民是第二次摊派青苗钱时开始前往京城的,戴石派人潜入难民中攀谈,发现这批人大多是失地的农户。农户没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只能前往京城鸣冤诉苦。这是古往今来的一大惯例,但这种情况一路的官员应该会上报才对。
要是难民到了京城,那事情可就大了。上至赵崇昭下至当地官员,都会被御史台骂得狗血淋头!
被骂还是小事。
问题在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没了土地?看来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青苗钱成了贪官污吏收敛钱财、兼并土地的工具。
谢则安眉头紧拧。
姚鼎言提出新法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在有些地方施行的情况也非常好,但对更多地方来说,青苗法并不适用。有农业合作社的分流作用在,青苗钱的影响稍稍削减,但抵不住有人想要政绩,威逼利诱手底下的百姓摊青苗钱。
这年头的百姓,大多畏惧官威,哪里敢反抗?县官不如现管!
谢则安说:“戴石,你去找张大哥,让他沿途建些临时房屋收留难民,让他们暂时不要进京。”交代完他又问,“离京城最近的一批难民在哪里?”
戴石说:“在南边,”他指着地图上地方,“离京城已经不远了。最近大家都在忙修路的事,一时没注意这么多,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得这么快。”
谢则安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这年头消息本来就传得慢,一时的疏忽很可能会使消息落后好几天。
不过一般来说难民都饥寒交迫,又没人组织,应该走得比较慢才是,这事儿实在不寻常。
谢则安对谢望博说:“大伯,我要去一趟。”
谢望博说:“你可要小心,他们都已经走到绝路了,难免会做出什么事来。”
谢则安说:“他们会走到绝路,不就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吗?”
谢望博一滞。他的思想虽然放得比较开,也不介意和农户往来,但骨子里终究还是有着世家的矜傲。静默片刻,谢望博还是正色说:“即使要做,也不需要亲入险境。虽然别人去也危险,但你不一样,你要是出了事儿,影响的会是一大批人。”
谢则安一愣,笑着说道:“能有什么事?陛下和大郎都在我身边安排了人,一般没人近得了我的身。再说了,我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自己也会使剑的。”
谢望博说:“你心里有底就好,万事都以安全为重。”
谢则安心中微暖,点头应是。
谢则安与谢望博道别,牵马准备出行。侍奉在院中的双生姐妹花瞧见了,连忙将披风送上。姐姐说:“官人万事小心。”妹妹说:“官人你去哪儿啊?”
谢则安朝她们笑了笑,说道:“有难民到了京城附近,我去瞧瞧。”他给妹妹说了个地名,叫她去告诉赵崇昭。
谢则安出城之后,赵崇昭才得到消息。他吓了一跳,连忙走出屋外:“来人,马上点二十人追上去,务必护三郎周全!”
禁卫领命而去,挑了二十个精锐快马加鞭地追上去。
赵崇昭既忧心谢则安的安全,又百思不得其解:都快过年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难民入京?大部分地方不都穿上棉衣盖上棉被了吗?他还有哪里没做好?
赵崇昭在屋里走来走去老半天,快步前往政事堂。
耳朵灵通的人不知谢则安一个。
赵崇昭抵达政事堂时,政事堂诸人都或快或慢地得了消息。谢季禹手上的是谢则安直接让人送过来的,连难民从哪儿出发、现在到了哪儿都弄得一清二楚。姚鼎言手上既有自己人送来的,又有谢则安让人送上的,两边一对比,姚鼎言发现了一点端倪。
姚鼎言不是迟钝的人,正相反,他比很多人都要敏锐。从底下人遮遮掩掩的情况看来,这几批难民会出现很可能跟青苗钱有关!
姚鼎言心神不宁。
赵崇昭说:“姚相,你们可曾得到消息?”
姚鼎言略过自己手里那份消息不提,说出了谢则安报上来的事儿:“三郎已经叫人送来了,这事儿来得突然,必须尽快查清楚情况才行。”
赵崇昭说:“三郎已经过去了。”他皱起眉头,“你们看派谁去把三郎换回来吧,三郎去太危险了。”
姚鼎言:“…………”
☆、第二零四章
连谢季禹都被赵崇昭这话弄得有点默然。
大家都担心谢则安,但怎么都不会说出“找个人去换回来”的话。这话要是说出去,赵崇昭说不定又会被骂得很惨:谢三郎的命是命,别人的就不是了?凭什么让人去把谢则安换回来?
赵崇昭也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他稍一沉吟,便让人去把李明霖唤过来。
李明霖伤在左边的胳膊,平日里倒看不出来,只有细看之下才能发现他左臂有古怪。他一进屋,不卑不亢地向赵崇昭见礼。赵崇昭已与谢则安开诚布公,对李明霖不复初时的敌视,不过事关谢则安的安危,他还是沉着脸对李明霖说:“三郎已将你遇刺的事告诉我,你再和姚相他们说说当日的情形。”
李明霖本来打算扛一把欺君的罪名,听赵崇昭这么说稍稍愣了愣。照谢则安和谢大郎那日的表现来看,明显是不愿让赵崇昭知道。谢家和皇家的关系一直耐人寻味,李明霖猜想了许多,最终决定坚定不移地站在谢则安那边。谢则安不想对外透露,那他就谁都不说。
李明霖见赵崇昭一脸了然,心中微凛,定了定神才开口:“那日下朝后我想起还有几桩事情没问明白,想去谢尚书家一趟。在经过谢尚书回家的必经之路时,一伙蒙面人突然出现,想对我下杀手。当时光线幽暗,我又身着官袍,看着和谢尚书有几分相像。这些人恐怕是冲着谢尚书来的……”
姚鼎言勃然大怒:“此事当真?”
对谢则安这个学生,姚鼎言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谢则安和他对着干,他气得暴跳如雷;谢则安没脸没皮地来向他赔礼请罪,他又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总的来说,姚鼎言对谢则安还是喜欢居多。要是不喜欢,谢则安的境遇不会把如今的顾骋、耿洵更好。
连他自己都舍不得折腾的混小子,居然有人敢设伏刺杀?
赵崇昭接过话茬:“当然当真!刺客已经转入天牢,我已派大理寺的人接手审问。”他叫张大德去把供词拿来,“他们一口咬定是赵奕景指使的,但三郎认为此中有古怪。这些人像是北边来的,极有可能是北狄人早些年派过来的细作。”
姚鼎言冷静下来。
赵奕景这位福王小公子他们都有所耳闻,瞧着赵崇昭对他宠爱无限,他们还觉得是不是又出了一个“谢三郎”。没想到这赵奕景居然会想出这样的昏招!难道是常年缠绵病榻,心思也阴暗偏激,见不得赵崇昭和谢则安那么要好?怪不得赵崇昭会翻脸无情,一转头就把人送到行馆软禁起来。
谢则安与赵崇昭之间的情谊,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岂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儿时玩伴”可以动摇的?
姚鼎言顿时便对赵奕景心生不喜。即使此事还有别的人在背后控制,赵奕景肯定也脱不了关系。这种心性的家伙,别人一怂恿就会屁颠屁颠地让别人当枪使,说不定到现在都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就一蠢货,比谢则安那小子差远了。
对于先前那么宠着赵奕景的赵崇昭,姚鼎言不免也带了点不满。
什么眼光啊这是!
姚鼎言正色说:“我亲自去一趟。”他面带薄怒,“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敢这样堂而皇之地对朝廷命官动手!”
谢季禹站出来说:“姚相且慢!”
姚鼎言转头看向谢季禹。
谢季禹入了政事堂,别的事都不掺和,和从前一样埋头做事,简直和徐延年一样滑头。他问:“季禹有话且说。”
谢季禹说:“姚相身居相位,不能轻易涉险,还是下官去吧。”
姚鼎言说:“你今日还要去司农寺忙活,我却清闲得很,季禹你何必相争。再说了,我又不是只身前往,哪有什么涉险不涉险的。”
谢季禹坦然说:“我担心三郎,想去看看。”
姚鼎言语塞。
过了一会儿他笑骂:“你倒是不避嫌。但我肯定要去的,你别劝我。”
赵崇昭说:“那就一起去吧。我也——”
赵崇昭话还没出口,徐延年已经先打断:“陛下您万万去不得!”
赵崇昭也知道希望不大,只能讪讪然地摆手:“那就姚相和谢参政去吧,派五十禁卫护卫左右。”他殷殷嘱托,“姚相,谢参政,你们也要小心注意,莫让歹人得手。”
姚鼎言脸色带上寒霜:“乾坤朗朗,我不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
另一边,谢则安出城不久,便瞧见了赵崇昭派来的人。见着那二十张熟悉的脸庞,谢则安停下来问:“陛下让你们来的?”
禁卫点点头。
谢则安明白赵崇昭的担忧,因而没拒绝他们的好意。他微微颔首,和他们一起奔赴那批难民的所在地。
约莫一个时辰之后,谢则安一行人抵达目的地。情形比他们所预料的还要惨烈,难民中的大多数人都瘦弱得叫人心生不忍,老弱妇孺被青壮们护在中…央,身上裹着不合身的破衣服,连补丁都来不及打。这大冬天的,大部分人居然赤着脚,那脏污的脚掌沾着污泥、和着血痂,看起来十分可怖。
听到马蹄声,青壮们警惕地朝中…央围拢,目光充满了敌意、防备和绝望。说他们是青壮也不太恰当,因为他们消瘦得厉害,有些人身上连上衣都没穿,冷得皮肤发红——甚至溃烂。
对上那一道道饱含愤意的目光,谢则安心中大震。
即使走过了不少地方,谢则安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他不由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的作为,他身居庙堂,往往极为轻易地作出决断,甚至会为了朝中平衡妥协让步。于他而言,“百姓”似乎也成了一个名词,一个毫无特殊性的名词,在某些时候即使必须牺牲一部分百姓也不会犹豫。
面对着眼前的惨状,谢则安猛地意识到他的每一个决断,绝不仅仅是朝堂上的博弈。
它会真真切切地落到一部分人头上——施加在这些人头上的到底是解难甘霖还是沾血利刃,全在他一念之间。
谢则安在离难民二十余米的地方就翻身下马。
他派人带着自己的信物去离这边最近的县城找大夫过来。
难民之中有不少伤病。
谢则安迈步走近,直直地走向一老翁。他敏锐过人,一眼看出这批难民隐隐以这